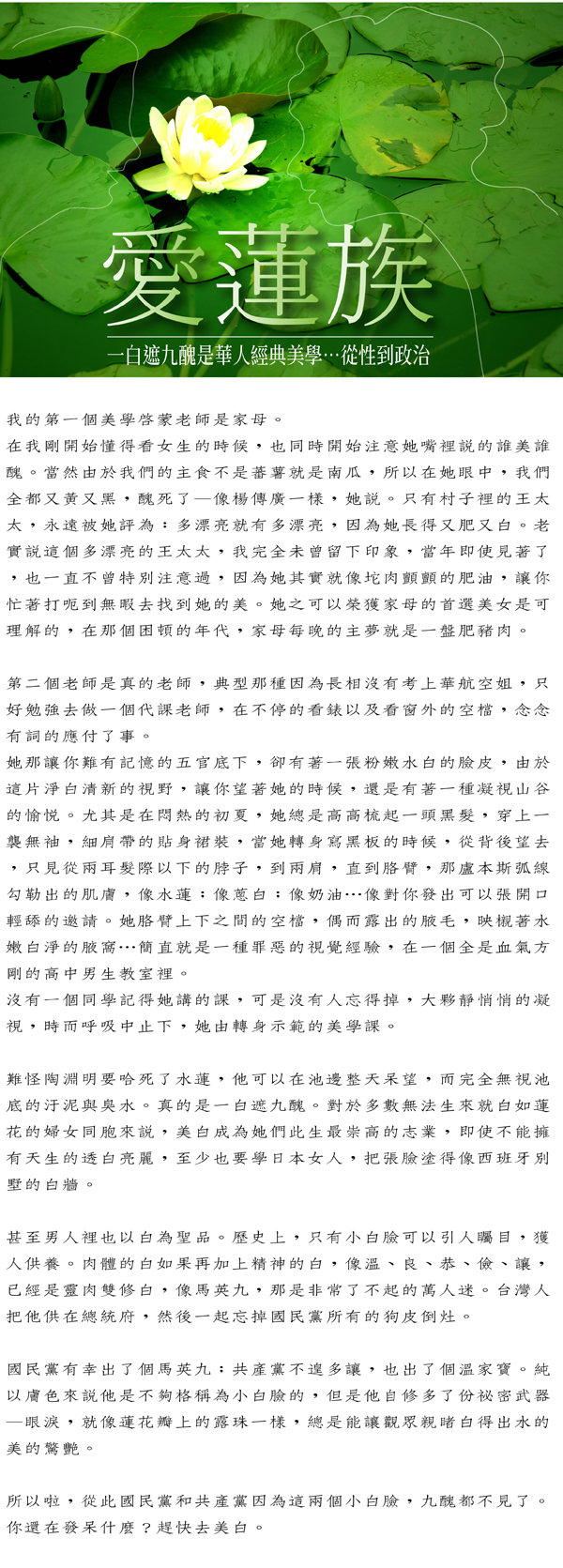18
9 月
Written by timchang.
Posted in: 國民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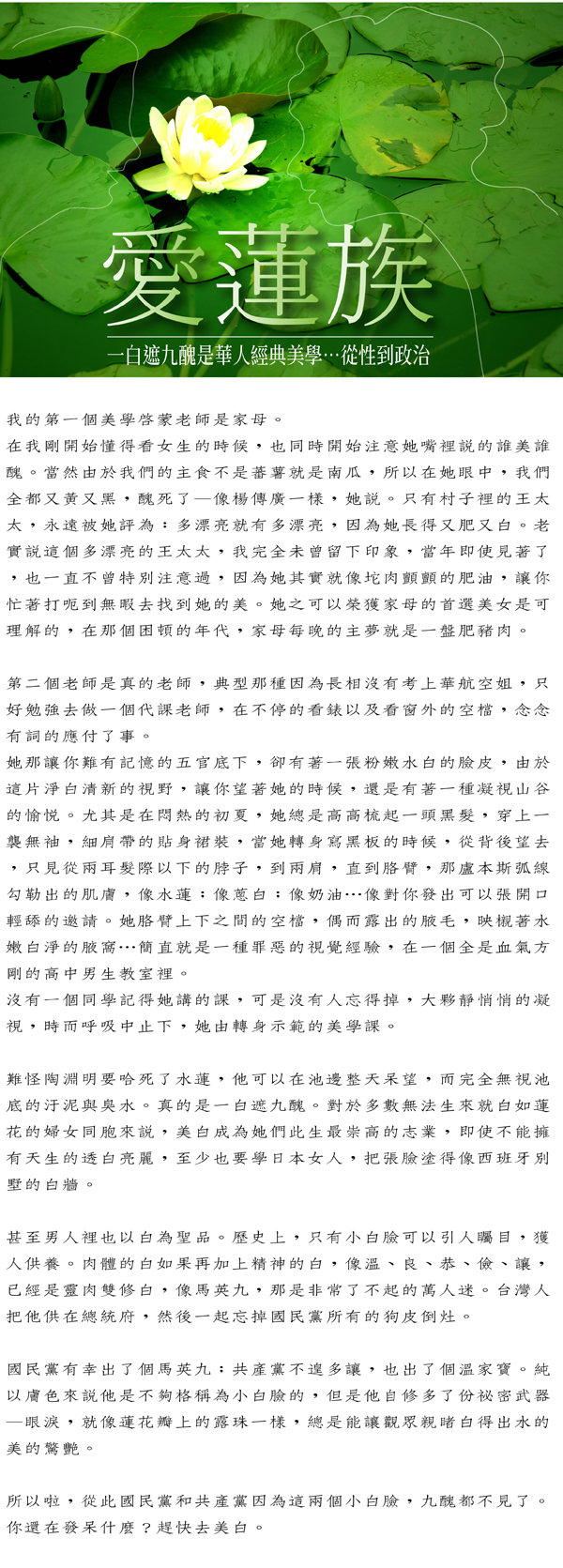
我的第一個美學啟蒙老師是家母。
在我剛開始懂得看女生的時候,也同時開始注意她嘴裡說的誰美誰醜。當然由於我們的主食不是蕃薯就是南瓜,所以在她眼中,我們全都又黃又黑,醜死了—像楊傳廣一樣,她說。只有村子裡的王太太,永遠被她評為:多漂亮就有多漂亮,因為她長得又肥又白。老實說這個多漂亮的王太太,我完全未曾留下印象,當年即使見著了,也一直不曾特別注意過,因為她其實就像坨肉顫顫的肥油,讓你忙著打呃到無暇去找到她的美。她之可以榮獲家母的首選美女是可理解的,在那個困頓的年代,家母每晚的主夢就是一盤肥豬肉。
第二個老師是真的老師,典型那種因為長相沒有考上華航空姐,只好勉強去做一個代課老師,在不停的看錶以及看窗外的空檔,念念有詞的應付了事。
她那讓你難有記憶的五官底下,卻有著一張粉嫩水白的臉皮,由於這片淨白清新的視野,讓你望著她的時候,還是有著一種凝視山谷的愉悅。尤其是在悶熱的初夏,她總是高高梳起一頭黑髮,穿上一襲無袖,細肩帶的貼身裙裝,當她轉身寫黑板的時候,從背後望去,只見從兩耳髮際以下的脖子,到兩肩,直到胳臂,那盧本斯弧線勾勒出的肌膚,像水蓮;像蔥白;像奶油…像對你發出可以張開口輕舔的邀請。她胳臂上下之間的空檔,偶而露出的腋毛,映櫬著水嫩白淨的腋窩…簡直就是一種罪惡的視覺經驗,在一個全是血氣方剛的高中男生教室裡。
沒有一個同學記得她講的課,可是沒有人忘得掉,大夥靜悄悄的凝視,時而呼吸中止下,她由轉身示範的美學課。
難怪陶淵明要哈死了水蓮,他可以在池邊整天呆望,而完全無視池底的汙泥與臭水。真的是一白遮九醜。對於多數無法生來就白如蓮花的婦女同胞來說,美白成為她們此生最崇高的志業,即使不能擁有天生的透白亮麗,至少也要學日本女人,把張臉塗得像西班牙別墅的白牆。
甚至男人裡也以白為聖品。歷史上,只有小白臉可以引人矚目,獲人供養。肉體的白如果再加上精神的白,像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,已經是靈肉雙修白,像馬英九,那是非常了不起的萬人迷。台灣人把他供在總統府,然後一起忘掉國民黨所有的狗皮倒灶。
國民黨有幸出了個馬英九;共產黨不遑多讓,也出了個溫家寶。純以膚色來說他是不夠格稱為小白臉的,但是他自修多了份祕密武器—眼淚,就像蓮花瓣上的露珠一樣,總是能讓觀眾親睹白得出水的美的驚艷。
所以啦,從此國民黨和共產黨因為這兩個小白臉,九醜都不見了。
你還在發呆什麼?趕快去美白。
Stay in touch with the conversation, subscribe to the RSS feed for comments on this post.